随着科技迅猛发展与互联网的广泛渗透,新蓝海、新赛道应时而生,并迎来了探索者的足迹。
从自动驾驶安全员到无人机飞手,从AI“翻译官”提示词工程师到活跃于屏幕上的短剧演员,他们或是科技革新的见证者,或是新蓝海的参与者。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了“新岗位”上的多位年轻人。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个体,在不经意间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出行以及娱乐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个人成长的见证,更是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缩影。
拍短剧,“赌”对了
本刊记者 杨琳
“拍短剧,赌对了。”
2024年初,演员许梦圆的第一部短剧正式播出。上线即充值破千万,抖音微博双热搜,让她打消了初期顾虑。这场“赌局”,她赢了。
去年,她几乎全年无休,付费短剧、免费短剧、品牌定制剧、文旅剧……各种类型都拍了个遍。这一年,动辄话题破亿的作品、涨粉百万的演员,以及越来越多知名的演员、导演官宣下场短剧,这个赛道好不热闹。
连外国人都逃不脱中国短剧的魅力。英国《经济学人》的文章提到,预计2027年中国微剧市场将超百亿,注意,是美元。
正如短剧霸总的一句经典台词“嘘——我不想从你的嘴里听到拒绝”,戏里的男主帅气多金专一,让人难以抗拒。戏外,短剧是超百亿美元的蓝海,有又爽又上头的剧情,不管行业内外,谁又能干脆说“不”呢?

剧组片场
“同学里混得最好的就是短剧导演”
许梦圆是幸运的,刚下场拍短剧,第一部短剧《裴总每天都想父凭子贵》就妥妥成了爆款。而在此之前,短剧从不在她的职业规划里。
“真没想到,突然间这部剧就被‘全世界’都知道了。”这部剧之后,找到她的剧本一下变多了,“最多的时候,一周能有几十本,看不过来”。
之后,许梦圆“灰姑娘三部曲”中的后两部也很快上线,在抖音的话题量均达数亿。
越来越多大众熟知的演艺人员加入进来 。“连刘晓庆老师都来拍短剧了!”聊到这儿,她也忍不住激动。
2023年时,她身边的很多人还在观望短剧市场,尤其是长剧出身的从业人员,他们口中,常有褒贬不一的声音。
待到2024年,形势一下子变了。
无论是入行新人,还是长剧导演、制片人,对短剧的态度更开放、更积极了。“大家都蛮想尝试一下。一些比较知名的制作人、导演、演员,都在问我:‘应该怎么开始?该怎么弄?’”
短剧势头涨得猛,和“快”分不开——拍摄快、制作快、播出快、反转快,演员曝光多、涨粉也快。
拿拍摄来说,四五天拍三四十集是正常节奏,甚至5天能拍90多集。
2025年春节档,导演张大鹏的作品《河豚小姐》上线,他笑称,“我已经拍得快‘冒烟’了”。“一个剧拍完之后,下个月就能播出了,以前从没遇到过。”倪虹洁近期监制、主演了《夫妻的春节》,她直接大呼:“我的天哪。”
按这种节奏,演员一年可以拍几十部短剧。其带来的拍摄机会和曝光量,都很可观。
“长剧的筹备、拍摄、后期、播出,可能得两年。这个时间,短剧能拍几十部。这几十部中,很可能会出几个爆剧,演员能迅速被熟知。”许梦圆坦言,“这给了很多新人试水的机会。”
一位201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毕业生说:“当年同班同学里混得最好的就是短剧导演。”
行业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达504.4亿元,比当年电影票房还多近80亿元。
国外观众也难以抵抗“霸总”的魅力。《经济学人》援引数据称,中国微短剧应用2024年海外收入达1.7亿美元。其预计,中国微剧市场到2027年将达140亿美元。而好莱坞的北美老家 ,在美媒“乐观”预计的情况下,2025年电影票房才90亿美元。
许梦圆也切身体会了一把短剧出海的红利。她的《裴总每天都想父凭子贵》拍了英文版,剧情一样,换了外国人主演;《闪婚成宠,首富大佬爱上我》配了日文配音,在海外视频平台的播放量都很高。
“我的社交平台一下多了好多国外粉丝,有日本的,有马来西亚的……有人给我留言:‘好喜欢你的《隐藏的真相 爱的考验》!’”许梦圆笑着说,“说的就是‘闪婚成宠’这部戏,到国外改名了,哈哈。”

《三井胡同的夏天》剧照

《夫妻的春节》片场

许梦圆在拍摄现场
短剧“进化”速度太快
如今,政府层面也看到了短剧的潜力,甚至“以身入局”。
去年,许梦圆接拍了两部列入国家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去旅行”项目的文旅短剧作品,一部是《三井胡同的夏天》,由北京市广电局指导,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北京广播电视台、抖音联合出品;一部是《职场小白》,出品单位是重庆丰都县委、县政府和央视频。
二者都是横屏短剧,主打精品。
《三井胡同的夏天》里,三井胡同、什刹海、烂缦胡同、天桥艺术中心、北京坊……观众可以“跟着短剧游西城”,欣赏美景美食。戏中热心肠又兼具正义感的“西城大妈”给不少人留下印象。
“这部戏把基层百姓的幸福具象化了。”能参与这样的项目,许梦圆觉得幸运,还有满满的骄傲,“出品方就是看了我的剧才选了我!”
如今,各大平台均在打造精品短剧集。题材越来越多,投资额也直线上涨。2025年春节档,于正的首部短剧《吉天照》上线,号称投资800万元,立刻成了行业热点。
“短剧的‘进化’速度太快了。”张大鹏感叹。
正是看到了短剧质量的提升,张大鹏改变了态度。“去年时,有人让我拍短剧,我还说‘别找我了’,但今年,我就来了。”他十分坦率。
张大鹏是拍广告、电影出身。他也直言,从整体看,短剧的质量依然有很大上升空间。“应该继续更多把短剧精品的‘样’给打出来,让更多人相信这个赛道大有可为,让更多人才加入进来。”
这也是行业共识。
对于许梦圆来说,她也希望短剧的这种势头能长期持续下去。“大家多些赛道、多点选择,遍地开花,这多开心呀。”
从“地面骑手”到“空中飞手”
本刊记者 马铭悦
想象一下,在迪拜40多摄氏度的烈日下,一位当地学生正在宿舍里等着享受下午茶。随后,窗外一架小型的无人机轻盈地降落。他从无人机携带的恒温箱里取出甜品和冰可乐,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可不是电影情节,是正在迪拜上演的真实场景。这背后不仅展现了中国技术的出海实力,更离不开一群新兴职业者——无人机飞手的支持。
罗锡坤便是其中之一。记者联系到他时,他正在迪拜出差。从“地面骑手”到“天空飞手”,从深圳到北京再到迪拜,罗锡坤用无人机再启新人生。

无人机外卖在迪拜
让中东消费者吃上“天空外卖”
2025年2月,罗锡坤被派往迪拜,当他踏上这片充满奢华与科技感的土地时,他感慨,沙漠里建起的都市名不虚传。
“我听这里的同事说,美团海外版(Keeta)在中东上线后,有些用户一天能点4到5次外卖!”罗锡坤对记者说,“迪拜地广人稀,气候炎热,高温下户外工作受限,外卖需求很大,传统运力根本不够用,所以无人机配送是一个完美解决方案,不仅环保节能,还能减少人力成本。”
无人机的应用不仅局限于外卖配送,它还在医疗领域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尤其是在紧急医疗物资的快速运输方面。“例如血浆配送对于时效有非常高的要求,无人机配送完全可以满足此类要求,能够在关键时刻挽救生命。”罗锡坤说。
2024年12月中旬,美团在迪拜拿到了第一张无人机配送的商业化运行许可证,并开通了4条航线。这些航线主要从餐厅或药房起飞,配送食品、药品和保健品。航线距离大约1~2公里,配送时间仅需5~6分钟。相关数据显示,到2030年,无人机配送服务预计将覆盖迪拜33%的区域。
“当地人对无人机配送感到非常新奇,看到无人机会竖起大拇指鼓掌叫好。”罗锡坤说。
在迪拜,罗锡坤的工作不再只是应急飞手,更多地参与到了无人机航线考察和测试中。他需要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和居民需求,设计最优的飞行路线。
罗锡坤说,他和团队成员们常常要反复测试,确保每一条航线都万无一失。此外,他发现,迪拜的居民对隐私和噪声问题和国内一样敏感。因此,他们在航线规划时,会尽量避开居民区,选择开阔地带作为起降点。
“这次迪拜之行,不仅拓宽了我的职业视野,更让我深切感受到海外对新技术的强烈需求。”罗锡坤兴奋地说,“我也没想到我能将外卖送到迪拜,能从一名普通骑手成功转型为无人机飞手,太幸运了。”


罗锡坤用无人机送外卖
在长城上也能点外卖
“在长城上搞无人机送外卖?这事儿靠谱吗?”
2024年夏天,当罗锡坤接到在八达岭测试无人机配送时,他心里直打鼓。在长城上空开设无人机“外卖航线”,这可比在公园用无人机送外卖刺激多了!
测试从八达岭长城的南九城楼开始,这里没有商铺,游客走累了连买瓶水都不方便。这种环境下,无人机配送显得尤为重要,但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
首先长城的地形复杂,信号十分不好。“垛口和城墙会干扰GPS信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人机需要具备更好的自主导航能力,能够在信号丢失时自行寻找路线。”罗锡坤所在的团队经过反复调试,升级出了“城墙模式”,让无人机学会绕开障碍物、悬停避让游客。此外,他们又接连攻克了天气、续航能力、载重能力等关键问题。
没想到长城航线开通的第二天就立了功。有位游客突发低血糖,载着功能饮料的无人机,仅仅5分钟就送达了外卖。“烽火台上收外卖,这服务也太穿越了!”游客举着手机录像,兴奋得忘了身体的不适。
“送完外卖的无人机,还能顺手把垃圾捎下山,每天帮清洁工少爬不少台阶。”罗锡坤骄傲地向记者介绍了无人机上实用的返程设计。
如今,在八达岭长城的南五城楼,扫码点外卖成了游客新乐趣。据了解,夏天高峰期时一天有超百单冰饮从天而降,孩子追着无人机喊:“妈妈,我也要在长城上吃雪糕!”
蛇年春节,更有游客为了体验无人机外卖,特意去爬长城。当游客在长城上吃到热乎乎的三明治时,飞手们也感到特别满足。
“以前觉得无人机送外卖是锦上添花,现在看有些雪中送炭了。”罗锡坤感慨道,现在的他越来越能感觉到这份工作的意义。
对于罗锡坤来说,无人机外卖飞手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次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罗锡坤说,他接下来计划考取无人机教员证,想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每一份经历都是为未来做积累。”罗锡坤说,从酒楼帮厨到外卖骑手,再到无人机飞手,他的职业转型充满了挑战,但也带来了无尽的机遇。
“我相信,随着技术成熟和政策支持,无人机将在更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罗锡坤说。
“新饭碗”,AI造
本刊记者 郭霁瑶
有人担忧AI正在抢走我们的工作。
当大模型以周为单位进化时,焦虑感正持续蔓延在职场的每个角落。
但硬币的另一面已然显现——AI在替代人类工作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新“饭碗”。
“与其担心被取代,不如思考怎么进化。”
“最大的门槛就是畏难情绪。”
当人们还在担忧自己被AI取代时,已经有不少嗅觉灵敏的新青年,在算法浪潮中拿到了新的入场券。
近期,《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走近几位找到AI“新饭碗”的年轻人,看看他们如何拥抱变化,开辟新事业。

工作中的赵可莹 本刊记者 郭霁瑶I摄
我给AI当“翻译”
北京亦庄,京东总部,赵可莹和同事正紧盯着电脑屏幕,嘴里小声念叨着:“求求了,这次千万别是胖头鱼。”
10多秒后,一条鱼头回望、鱼尾回甩的红色锦鲤出现在屏幕上。不同于传统的锦鲤形象,布满鳞片的鱼身暗含着生肖蛇的意象,整体造型又与巳蛇的“巳”字神似。
“这下成了!”赵可莹握住了一旁同事的手。
这个融合非遗剪纸与现代审美的作品,是京东与河北蔚县文旅局合作的“AI+非遗”项目成果。项目早期,赵可莹每天都要经历无数次这样的“盲盒”时刻。
“为了这个项目,我们给言犀大模型‘喂’了好几千张剪纸图样,就是为了构建AI对剪纸的美学认知。”赵可莹指着屏幕上的剪纸纹样图库说,“后来随着高质量数据的增加和大师不断碰撞,提示词经过优化后,大模型越来越懂了。”
赵可莹是这个项目的提示词工程师,用她的话说,自己的日常工作就是给AI当“翻译官”和“老师”。“就是把人类的需求翻译给AI。在这个过程中,还要给AI‘喂’资料,引导它学习。”
这个新兴职业的日常总是充满了“惊吓”和惊喜。“初期生成的图案常让人哭笑不得。”赵可莹调出对比图向记者展示,左侧是体形笨拙的“胖头鱼”、比例失调的大鲇鱼,右侧是优化后融入各种元素的成品。其中既有融合“蛇拿九稳”“蛇么都好”“蛇歇薪涨”等网络热梗的新潮剪纸,也有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向日葵等广为流传的世界名画剪纸,还有索菲亚大教堂、天坛等时下爆火的打卡地图案。
“这就是提示词不同的结果。”赵可莹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如果你觉得AI笨,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找到对话的钥匙。”
说起来容易,但这个新兴职业远非输入指令那么简单。赵可莹告诉记者,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提示词工程师,不仅要有将复杂需求转化为清晰指令的能力,还要熟悉AI模型的运作原理,拥有计算机科学基础。“既要懂人,又要懂AI。我自己就是从算法工程师转型来的。”
如今,提示词工程师已逐渐成为“大厂必备”。但这一岗位常被视作是AI发展尚不成熟的阶段性产物,有观点认为其终将消失。
对此,赵可莹思考后分析:“未来可能会在现有岗位上衍生出更高级的角色,比如AI交互设计师。”
面对瞬息万变的未来,这名“95后”丝毫不畏惧:“与其担心被取代,不如保持开放的心态,思考自己怎么进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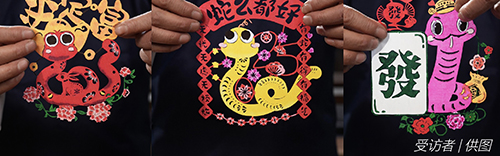
融合网络热梗的剪纸图案

AI早期生成的“胖头鱼”图案

AI优化后的剪纸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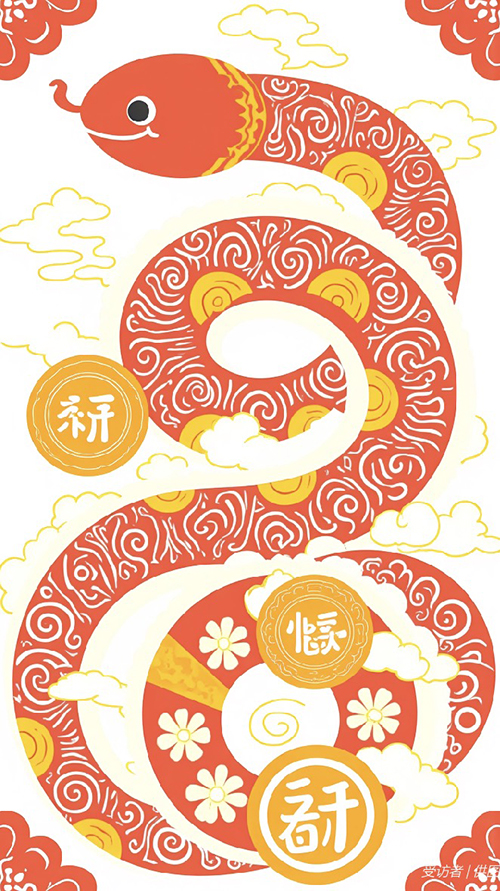
AI生成的蛇形剪纸图案
最大的门槛就是畏难情绪
“有DeepSeek和ChatGPT以后,怎么当编辑?”2月的一天,魔云兽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作为从业多年的图书营销编辑,他比谁都清楚这个问题的意义。
每天,魔云兽都在切换着双重身份:白天在出版社策划新书营销方案,晚上下班后化身AI科普博主。打开手机,几百号人的微信群不停弹出新消息提醒——又有一位成员分享了自己用AI生成的文案修改心得。
“虽然赚了些钱,但我现在离稳定变现还远,更多是兴趣驱动。”魔云兽坦言,“公众号、短视频账号会定期更新文章,主要是AI使用攻略。另外,我还建立了线上社群,发布一些付费知识内容。”
2023年冬天,ChatGPT横空出世,让这位文字工作者经历了职业生涯最剧烈的震荡。“‘我的主业是推书,但AI比我写得快,那我干这活儿的意义何在?’我问了AI这个问题。”魔云兽回忆道,当时AI回复了很长一段安慰文字,仔细分析了作为人类的他做什么能不被取代。
“AI告诉我,我的定位应该从‘内容流水线’向‘内容策划师’转变,也就是成为文章的导演。”就此,魔云兽开始琢磨如何运用AI协助自己写作。
经历了前期的单独摸索后,魔云兽决定建个交流群。“自己琢磨太慢了,得让不同背景的人碰撞。”现在群里有各色背景职业的人,他们中既有想降本增效的公司职员,也有试图用AI创作网文的家庭主妇。“大家都是奔着一个目标,通过AI提高工作效率。”
“我发现普通人运用AI,最大的门槛就是畏难情绪。我在科普AI的过程中,也是在不断突破自己的畏难情绪。”魔云兽说。
这样的探索并非孤例。随便点开某个内容平台,“AI副业月入过万”的标题总在制造焦虑,知识付费区挤满速成教程。“确实有赚到很多钱的,但市面上很多内容是粗制滥造的AI洗稿。”在某社交平台一搜索“DeepSeek使用攻略”,蹦出来的许多都是充满“AI味”的流水线稿件。
“我自己写科普文章也会借助AI。但我发现,AI快速‘跑’出来的稿件和自己仔细打磨的文字,差距还是很大。”魔云兽坦言。
说着,魔云兽分享了AI生成的诗集。“的确写得很棒,这押韵、这修辞都高级得没话说。但……”他苦笑着摇头,“那种能让人泪流满面的力量还是出不来。像前段时间外卖员用自己生命体验写下火爆全网的诗歌,现在的AI还是写不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赵可莹、魔云兽为化名)
我给无人车当“教练”
本刊记者 孙晓萌
在长江与汉江交汇的武汉街头,程一凡坐在车里,看着自己测试的“萝卜快跑”无人车从容穿过车流。同一时刻,1000公里外的北京,李明正在虚拟世界中的“另一个武汉”里“跑车”。仿真系统里,无人车突然遭遇暴雨中逆行的电动车,系统要眨眼间修正车辆行驶轨迹。
给无人车当“教练”,“教”汽车直行、转弯、刹车、避让,让车比人开得还“老练”,就是程一凡和李明的日常工作。他们正是技术进步催生出的新职业从业者,两位年轻的自动驾驶探路者,在现实与虚拟中,共同构建着未来的出行方式。

测试负责人程一凡正在与团队成员讨论工作
从“有人辅助”到“无人驾驶”
回顾自己最初进入汽车行业的场景,辽宁汉子程一凡说:“2015年,我在一家主机厂参与汽车主动安全以及行车辅助工作,那时大家都意识到汽车智能化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他举例说:“主机厂从最开始的装配角色想转变为有自主开发功能的角色,一些为主机厂提供零配件的供应商也在提升技术能力。”
在他后续的职业生涯中,智能化几个字贯穿始终。“后来我在一家车载毫米波雷达公司工作,做一些安全和驾驶辅助功能应用层产品设计和测试工作。加入‘萝卜快跑’之后,我开始参与L4级别无人车功能测试和落地推进。”
在程一凡看来,国内自动驾驶技术近年来发生过几次大变化。“自动驾驶技术最开始围绕的是‘主驾有人’驾驶辅助,它的功能安全要求是不一样的。到了无人驾驶阶段,为了保障无人车在公共道路上能够安全行驶,包括测试里程、驾驶里程无故障率、无接管率等都要求有数量级的提升。”他解释道。
“我们L4级自动驾驶安全测试里程累计超1.3亿公里,从‘萝卜快跑’的记录来看,自动驾驶出险率仅为人类驾驶员的1/14。”程一凡说。自动驾驶技术被划为5个等级——L1到L5,L4意味着特定环境下,无人车高度自主,无须驾驶员人为干预。
现在,程一凡带领着一个20人的实车道路测试团队,日常工作是进行公共道路上的自动驾驶测试。“除了制定测试方案,还要进行自动驾驶功能实车测试,我会安排工程师和车内安全员协同配合,针对各种测试场景做具体执行、数据收集和问题反馈。”
程一凡所带团队承担的是实际上路测试,但他认为未来自动驾驶最需要的人才可能是数据处理方面。


行驶中的无人车
在虚拟世界预演危机
李明就是成天和仿真测试数据打交道的质量检测工程师。
从医学影像设施跨界到自动驾驶仿真测试的李明,在被问及二者间的差异时,他说:“我认为这二者相似多过不同,眼底医学影像判断和红绿灯灯色识别,本质都是图像解析的追踪—检测—识别流程。”
为什么跨界自动驾驶?李明总结是“大势所趋”,“我留学时参加过东京日产总部的自动驾驶相关实习,日本叫车辆的智能手机化。当时全球车企都在追随这个趋势,因此我决定回国做我们自己的无人车”。
在用于测试的虚拟世界里,构建和现实世界一样完备的场景,是李明PnC(Planning and Control)仿真测试工作的一部分,“像武汉的高速高架、停车场泊入泊出、环岛这类都是需要构建的场景”。
随机路测则是李明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它又叫随机交通流测试,比如我们在仿真系统里构建一个武汉路网场景,里面会有一些随机的车流,主车在里边跑。它其实是模拟路上的真实情况,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很多问题,问题解决会促进研发迭代和算法进步。”李明在采访中努力解释着一些关键名词。
现在,仿真系统里的武汉虚拟路网正不断扩大。“我们每天会跑超大规模的数据集,数据量越多,遇到的问题越多。”李明说,“所以我会说没有罕见案例了,这也是行业共识。”
真实世界里的一个问题(比如容易诱发事故的路况)被修复后就消失了。“实际路测中,修复后想重新验证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如果问题价值高,就需要仿真测试来做问题的后验。”李明如此解释。
“仿真测试这几年进步很快,几乎有深度学习专业的科研院校,或多或少都在进行AI或者自动驾驶仿真工作,我们也在交流和学习。”李明对此颇有感触,“去年特别火的world model(世界模型),就是在由AI构建的世界模型里去进行仿真测试,还会构建自动驾驶的能力和场景。”这使得自动驾驶仿真测试变得更轻松。
“从事自动驾驶行业像在攀一座大山,翻过一座山之后还会有另外的山,一直有新的问题要解决。”他总结这个行业最需要的特质,“想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一定要非常乐观。就像我的工作不容易被看到,但是对整个行业而言很重要。还有最重要的是保持热爱。”
2025年春节,程一凡带着侄子侄女体验无人车。“孩子盯着无人操控的方向盘问:‘叔叔,这是魔法吗?’”孩子的提问让他意识到自动驾驶的更深层意义。“我觉得我给下一代做了榜样,不敢说特别好,但是希望能激发孩子对新事物的好奇心。”
(应受访者要求,程一凡、李明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