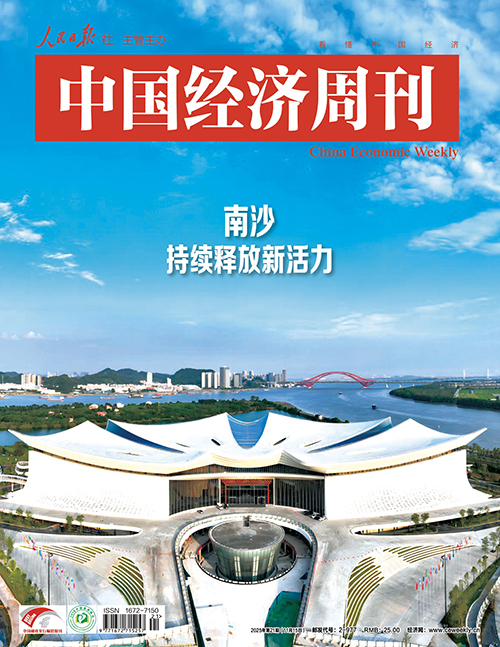文|言懿
什么是“租金”?
在经济学中,“租金”或更准确地说是“经济租金”(Economics Rent),指的是任何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资本)所获得的超过其机会成本的收益。
举例而言,一位顶级职业运动员,年收入高达1000万元,但即便年收入只有200万元,他也愿意继续从事该职业(这200万元是他愿意留在该行业的最低报酬),那多出来的800万元就是这位运动员的“经济租金”,源于其独特的天赋和难以替代的技能。
在寻租理论(Rent-seeking)里,寻租行为指的是个体或团体通过非市场手段获取超额收益,而不是通过创造财富或增加生产效率来获得收益。通俗地说,寻租行为就是不靠“创造价值”赚钱,而是把精力用在“找关系、占便宜”来获利。
这一理论清晰揭示了为何行政审批部门常成为腐败高发区:牌照的稀缺性使审批者掌握分配超额利润的权力,从而形成寻租空间。

一
然而,若将视线从有形的“牌照”与“指标”,转移到无形的“时间”,我们会发现:对时间的控制同样构成一种重要权力。一旦审批者拥有决定“快与慢”的自由裁量权,等待就变成申请人的成本,加速则有了价格——时间由此被转化为可套现的“租金”。
在许多腐败形式中,拖延或加速流程成为一种寻租和设租手段。
比如,当企业急需资金“续命”,等待就意味着真金白银的成本和生存风险。此时,“时效”本身便成了一种可供交易的稀缺品。寻租者正是利用这种时间压力,通过人为设置障碍、拖延流程,将本应正常的“效率”异化为一种需要额外付费的稀缺服务。
这笔为“加速”而付出的费用,本质上就是被勒索的“时间租金”。这种寻租行为极其隐蔽,一句“流程比较复杂”或“材料需要研究”,就成了拖延勒索的完美借口,为其寻租行为披上“合规”的外衣。
二
利用对时间的支配权来设租,是极具危害性的隐蔽寻租行为。
比如,在资本市场领域,对一家拟上市公司而言,早一天上会,或许就意味着能够把握更有利的市场窗口,获得更高的发行估值。在这种背景下,时间,就是指数级的金钱。于是,围绕“审核节奏”的寻租空间便悄然洞开,滋生出隐秘的灰色利益链条。一些经营主体打着“财务顾问”“上市咨询”的幌子,行利益输送之实,通过支付高额费用,换取审核流程中的“优先权”或“加速权”。
如果那支决定节奏的笔,不再以企业质地和市场公允为准绳,反而精准地为支付了“时间租金”的投机者“清障开道”,它在客观上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机制。当市场竞争的赛道不再公平,最终胜出的便不再是质地最优、最具潜力的创新者,而是那些最擅长勾兑资源、“购买时间”的寻租者。
又如,在金融机构风险处置过程中,当一家机构因资不抵债被接管处置,其债权人往往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此时,处置组手中掌握着一项重要的裁量权:决定清偿顺序。
对同样身为债权人的其他金融机构而言,“流动性就是生命线”。一笔关键资金,是先兑付给张三,还是先兑付给李四,不仅是时间先后的问题,更可能直接关系到另一家机构的风险敞口与生死存亡。
掌握资源分配权力的人,无须直接创造价值,仅通过设定兑现的先后顺序,便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对于流动性命悬一线的机构,早日兑付的诱惑足以使其甘愿支付额外代价,换取一线生机。
再比如,一个停车场也能产生“小官大贪”。看似不起眼的停车场管理员,掌握着“车位分配权”,可以决定一个人的车能停在离大门多远的地方。对普通人来说,多走几步路无伤大雅。但对于那些需要频繁拜访且视时间为生命的商界人士,一个“专属车位”所节省的时间与精力,便成了一种值得“投资”的特权。一条烟、一顿饭,就可能换来长期的“时间便利”。
它揭示了一个冰冷的现实:即便是微小权限,也存在被异化和滥用的风险。
三
这些场景共同指向了“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特征:相关行为常以市场化、合规化的形式为掩护,通过延迟兑现、优先安排等方式,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在对金融领域腐败问题的研判中,社会的关注点往往集中于重大涉案金额、违规放贷规模等显性指标。然而,“时间寻租”这一现象警示我们,比直接窃取金钱更可怕的是,对资源配置规则的根本性侵蚀,带来了更为隐蔽和深远的负面影响。当资本的流向不再完全由项目质量与市场前景决定,而是被获取“时间优先权”的能力所左右时,便会形成破坏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损害资源配置效率的机制性障碍。
因此,打击金融腐败,不仅要严密监控异常的资金流动,也要敏锐识别并有效规制那些将时间要素作为寻租工具、扭曲市场秩序的“腐败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