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经济前景光明,信心在哪里?底气在哪里?活力在哪里?《解码中国经济——12 位经济学家的思享课》一书由《中国经济周刊》编写,特邀黄奇帆、刘世锦等12 位著名经济学家,深入解读中国经济未来走势。
刘世锦认为,在改革工具箱内,能够找到不少有立竿见影之效的改革举措,产生短期效应。那些中长期见效的改革,如能尽早启动和推进,也能形成积极预期,对短期稳增长发挥正面作用。
以下内容为书籍节选,内容有删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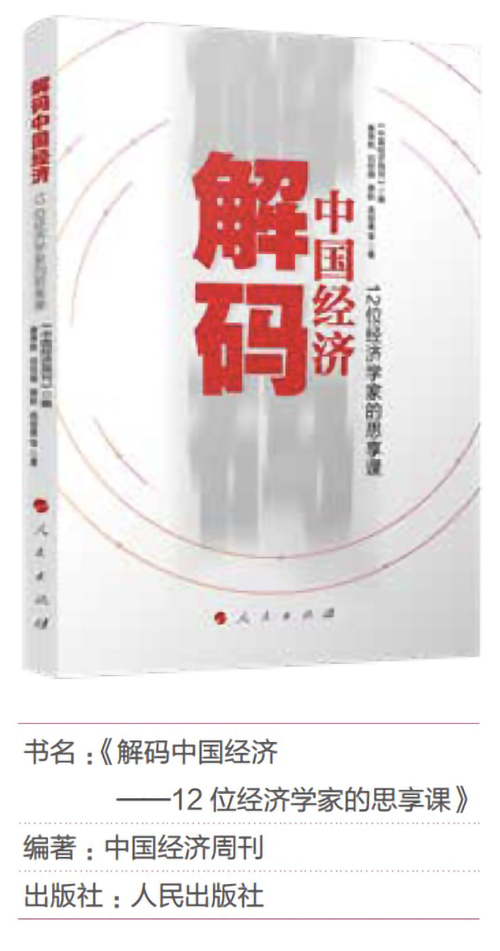
文|刘世锦
当前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是需求不足。需求不足不仅影响消费领域,还波及就业、财政等多个方面,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我们不仅要认识到需求不足所引发的问题,更要深入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尤其是背后深层次的根源。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与原因,本身是两个不同的议题,需要明确区分开。当前,我们很容易将这两者混淆,因此,必须厘清思路,准确识别问题的成因,这是寻找解决问题线索的重要前提。
扩大消费的关键在源头治理
当前,扩大消费成为热议话题,但关键在于找准重点和痛点。我认为有以下三点:首先,应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重点发展包括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信等在内的服务消费;其次,应关注中低收入群体;最后,应坚持以人为中心,推动权利平等的市场化和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消费需求不足,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长期以来,我们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倾向于重投资而轻消费;其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相对滞后;再次,城市化质量偏低;最后,收入差距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其中的逻辑和方法至关重要。
我借鉴了治理污染的思路,将扩大消费的策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末端治理。简单来说,就是像直升机撒钱一样,直接发放消费券或现金以刺激消费。对于这种观点,我们需要思考它是否真的有助于扩大消费。确实,短期内,如果一个城市在某个月发放消费券或现金,鼓励大家购物,那么这个月的消费占比无疑会上升。然而,到了下个月或第二年,如果消费水平本身较低,那么,这种提升很可能是暂时的,消费水平最终还是会回落。
此外,还存在消费倾向的问题。如果采用“直升机撒钱”的方式,亿万富翁也可能获得这笔钱,但对他们来说,这笔钱并无实际意义。即使将钱发放到低收入群体手中,他们可能会因为多买几个面包而感到高兴。然而,他们真正担忧的是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发放消费券或现金,无疑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二种方式,我称之为中端治理。以当前典型的减轻债务负担为例,我们的债务负担多是欠银行的债务。假设我们实施一项刺激政策,将资金提供给经济主体,他们很可能会用这笔钱来偿还债务,而大部分钱最终又回到了银行。那么,银行拿到这些钱后能否顺利贷出?事实上,目前银行面临的问题也是需求不足,有一种说法是借款人不足,人们不愿意借款。
也有一些情况是,某些主体之前欠企业的钱,现在通过清理账款来偿还。偿还后,拿到钱的企业可能会发放一部分工资,从而间接扩大消费,但这部分消费的具体规模仍不确定。此外,这些经济主体在减轻债务负担后,为了稳增长,他们可能仍然会选择扩大投资或上马大项目,实际上是在进一步扩大供给,而当前的问题是消费需求不足,这种做法反而加剧了供需矛盾。
第三种方式是源头治理,即将资金用于扩大消费,特别是针对服务消费需求效应最强的人群和环节。这不仅仅是一次性救助,更重要的是“花钱建新制度”,形成长期可持续的机制,从而有效纠正消费需求的结构性偏差。
扩大消费需求
特别是服务消费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具体来说,在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提升农村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方面,都提出了不少深化改革的要求,现在需要的是切实落实这些改革措施。
正如上文所讲,我们当前正面临需求不足的压力,现在需要实施一些刺激政策。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为结构性改革争取时间。
改革往往被认为是慢变量,远水不解近渴。事实上,在改革工具箱内,能够找到不少有立竿见影之效的改革举措,产生“今晚公布,明早涨停”的短期效应。即使那些中长期见效的改革,如能尽早启动和推进,也能形成积极预期,对短期稳增长发挥正面作用。
现阶段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服务消费,应着力推动以下三个方面的结构性改革。
首先,以扩大中央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事权为突破口,加强社会保障和提升人力资本的能力建设。在中央与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事权划分方面进行合理调整与优化。养老医疗保障的基础部分,如养老保障的第一支柱(即基础部分),以及义务教育范围的拓展(如当前正在探讨的是否将其扩大至高中教育阶段)等事项,可划为中央政府事权。
而社会保障的其他方面,比如,养老保障的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保障性住房建设、教育培训等则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
具体而言,应当大力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市民群体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保障水平。例如,继续推进政府收购滞销住房并将其转化为保障性住房,然后以租赁或者出售的方式提供给新市民。农民要由进城打工者转为在城市家庭团聚、安居乐业。
增加保障房供应可以扩大房地产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家庭团聚可以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与此同时,可适当降低个人和企业缴费水平,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促进企业增加投入、个人扩大消费。相应减少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事权,缩小其事权财权不平衡缺口。
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充实社保基金。可以考虑从当前的刺激计划资金中拨出一部分,专项用于养老金的发放。
更重要的是,应抓紧探索国有权益资本划拨到社保基金。理论上,国有资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全国人民的社保基金。2023 年国有资本权益总额为 102 万亿元,国有金融资本权益总额为 30.6 万亿元,两项合计为 132.6 万亿元。
可以考虑分步稳妥地把较大规模的国有金融资本划拨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减少居民缴费,提高居民养老金收入,在短期内尽可能明显缩小城镇与其他群体的养老金收入差距。把国有资本划拨给养老保险,将会把大量预防性储蓄转化为现实的消费能力,直接增加消费需求。
现阶段加强社会保障和提升人力资本的能力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进展,也是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体现。应争取用 5~10 年时间,逐步缩小并基本消除城乡之间、城市内新老市民之间在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上的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在适宜水平上均等化的目标。
其次,以城乡接合部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流动、融合发展,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
在城乡接合部开展城乡居民土地权利均等化、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利用的改革试点,并以此为牵引,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我国城市核心区建设已达到较高水平,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堵。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 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镇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容纳 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的是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这一区域也适合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集聚,基建和房地产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
通过提高城镇化的比例和质量(缩小以至消除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力争用 10 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由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 4 亿人口增长到 8 亿~9 亿。提出并推进实现这一目标,对延长中速增长期,打破需求约束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以调整经济活动中所有制属性的界定范围为突破口,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创新完善,创造更多的较高收入就业机会。
(本文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