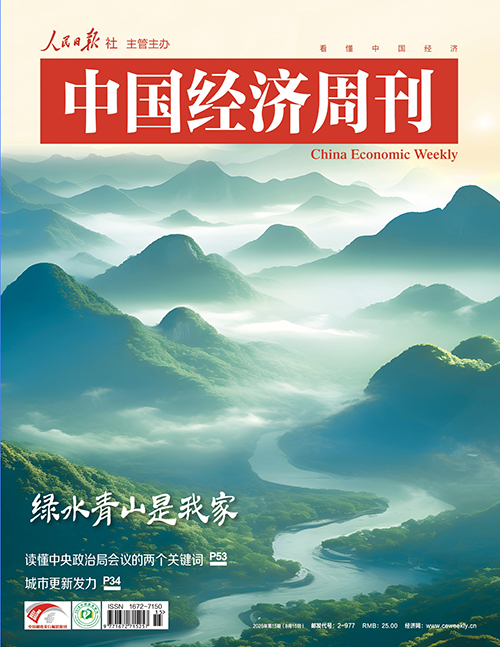编者按:
中国经济前景光明,信心在哪里?底气在哪里?活力在哪里?《解码中国经济——12 位经济学家的思享课》一书由《中国经济周刊》编写,特邀黄奇帆、刘世锦、蔡昉等12 位著名经济学家,深入解读中国经济未来走势。
蔡昉认为,经济增长的做大“蛋糕”效应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改善的分好“蛋糕”效应,有助于在应对人口结构新变化中具有足够回旋余地,在运用政策中产生削峰填谷效应。以下内容为书籍节选,内容有删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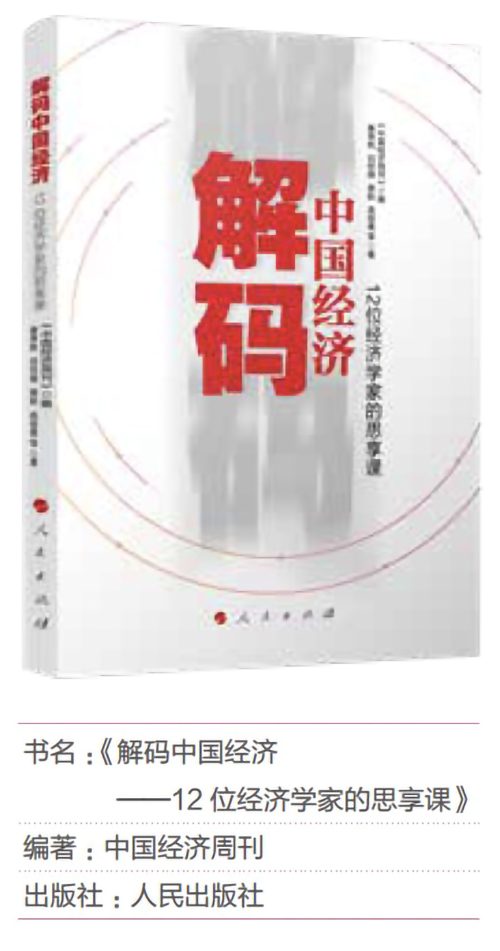
文|蔡昉
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按人均GDP衡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这个阶段,我国经济仍将保持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以及充足的增长潜力,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统一。
在这一进程中,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更充分释放劳动力丰富的传统优势潜力,为发展方式转变和增长动能转换赢得时间。促进新要素组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推动经济增长转向新动能轨道,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潜在增长能力。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持续改善民生,将显著增强消费需求及其引导的投资需求,从而推动以强大的内需实现潜在增长率。
不断提高资源整合水平和统筹配置层次
按照要素供给潜力和生产率提高趋势预测,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仍然足以支撑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合理的区间。如果能够实现这一潜在增长速度,我国就能够在2035年实现按人均GDP标准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为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成色十足的物质基础。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上述增长潜力预测结果。
第一,从当前到2035年,我国正处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进而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从中度老龄化到重度老龄化的人口转变阶段。预测的潜在增长率,明显高于处在相同老龄化阶段(即老龄化率在14%~24%之间),以及处在相同人均GDP阶段(即人均GDP在12000~24000美元之间)国家和地区的实际增长率。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关键领域推进的力度和成效,可以分别从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两个方面创造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水平,并且这个提高幅度即改革红利没有上限。
第三,我国在推进14亿人口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具有超大规模市场的内需优势,通过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用市场化办法激发需求和优化供给,经济增长潜力便可以转化为现实经济增长。
合理、合意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将为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提供更多和更高质量公共品,既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遵循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支持政策体系,涉及基本公共服务诸多关键领域的完善和改革,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目标完全一致、路径高度重合,很多政策措施也可以达到毕其功于一役的效果。
经济增长的做大“蛋糕”效应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改善的分好“蛋糕”效应,有助于在应对人口结构新变化中具有足够回旋余地,在运用政策中产生削峰填谷效应。虽然少子化和老龄化都带来挑战,但在我国目前所处的人口转变阶段,在老龄化提高人口抚养比的同时,少子化具有降低人口抚养比的效果,因而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互抵消关系。这样,从整体效果上来看,“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尚不会一下子便转化为“生之者寡、食之者众”。
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在2023—2035年期间,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预计提高13.9个百分点,由于少儿人口抚养比同期降低8.1个百分点,使总体人口抚养比的提高幅度相对和缓,仅为5.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包括人口支持政策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有条件也有必要不断提高资源整合水平和统筹配置层次,特别注重优化存量资源的使用和增量资源的配置,以此支撑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实现提升全人群福祉水平的目标。
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的政策着力点
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要求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按照全局性、综合性的要求拓展工作思路的深度和工作领域的广度,更加重视采用引导和激励的办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改革,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并与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共同进行顶层设计,同步推进政策实施和制度建设。
第一,以生育、养育、教育阶段为重点,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覆盖水平,同步实现降低“三育”成本、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率,进而达到全面提升人口素质的任务目标。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依靠劳动力数量的传统人口红利虽然消失,但更高人力资本构成的新人口红利,仍有巨大的提升余地和贡献空间。
一是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在政府、社会、家庭之间形成激励相容、治理协同和推动同步的局面,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家庭生育意愿与社会适度生育率最大限度的一致性。国际经验显示,总和生育率2.1这个更替水平,不仅是保持宏观人口稳定的社会目标,也是家庭普遍期望的孩子数。
实际生育率偏离这个水平,或家庭期望生育意愿与实际孩子数不一致,根源便是家庭和社会之间的激励不相容。因此,持续推出生育友好型政策,必然包括降低“三育”成本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扩大和均等化供给,有助于提高激励相容的水平,达到提高生育率的目标。
二是通过提高生育和养育服务
的公共化水平,提升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能力,统筹育幼资源使用,完善生育休假制度,加大个税抵扣力度,在降低服务成本的同时提高服务质量。既然将提高生育率作为社会目标,说明提高人口再生产的可持续性具有正外部性,符合全社会长期、共同利益,因此与之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公共品的性质。诚然,在现代化过程中,公共品供给规模和范围的扩大是一个一般规律,中国面临的人口结构变化,无异于指出了扩大公共品供给的优先领域——建立和完善人口再生产支持政策体系。
三是因应人口发展趋势性特征对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培育方式提出的新要求,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大资金投入和各方面资源统筹力度,扩大各级各类优质教育供给,逐步把教育向学前乃至托幼阶段前移,提高高中阶段教育免费范围和普及率,让教育和培训贯穿劳动者就业全过程,在全生命周期培育人力资本。为了开启新人口红利、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培育新人力资本是关键抓手。
在以人工智能发展为特征的技术变革中,人力资本积累的性质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从人与人之间的人力资本禀赋竞争,越来越转化为人类智力与人工智能之间的竞争;二是应对人工智能冲击的人力资本,越来越需要在全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覆盖以“一老一小”为两极的所有年龄。这两个新特征都意味着,教育的公共品性质更加突出,政府在终身学习体系中的支出责任更加重要。
第二,加快培育现代化急需的人力资源,提高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和匹配水平,解决好结构性就业矛盾。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和总人口相继转向负增长,我国就业的总量性矛盾有所缓解。与此同时,就业形势也呈现新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人口发展呈现新的趋势性特征条件下,青年就业群体受教育程度高却缺乏工作经验,大龄劳动者工作经验丰富却受教育程度低,因而都面临更大的就业困难;另一方面,技术变化和经济数字化转型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不断提高,与劳动者存量结构产生矛盾,也引起就业形态变化。
随着上述两方面因素对就业的影响逐步加深、加大,我国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便日益突出。从应对政策的角度,这要求完善就业优先战略,丰富积极就业政策内涵,充实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从政策辅助对象来看,更加关注各类青年就业人口和大龄劳动者等重点群体。在此基础上,着力解决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的矛盾,通过提供更加精准对路的公共就业服务,帮助劳动者获得新技能并增强就业适应能力,从破解“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
第三,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为核心,满足老年人的基本养老保障和基本养老服务需求,提高老年人群的生活品质。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不仅是增进老年人福祉的必然要求,也是通过充分发挥大龄劳动力的庞大人力资源和老年人口的消费力,让大龄人群和老年人群体发挥出“银发力量”的关键之举。
因此,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政策领域跨越社会保障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需要在目标和手段相一致的前提下协同发力。
推进实现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必须关注大龄人群和老年人群体。一是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和服务的供给水平、覆盖率和均等化程度,确保老年人生活品质的提高与现代化进程同步推进。二是创造条件增强大龄劳动者的就业意愿和就业能力,提高老年人的经济社会参与水平,为有意愿的老年群体创造多样化、个性化的就业岗位和社会活动形式,扩大和延续人口红利。三是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满足老龄社会的特殊消费需求,在免除老年人后顾之忧的前提下,持续发挥他们作为消费者的积极功能。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本刊记者王红茹采访整理,稿件经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