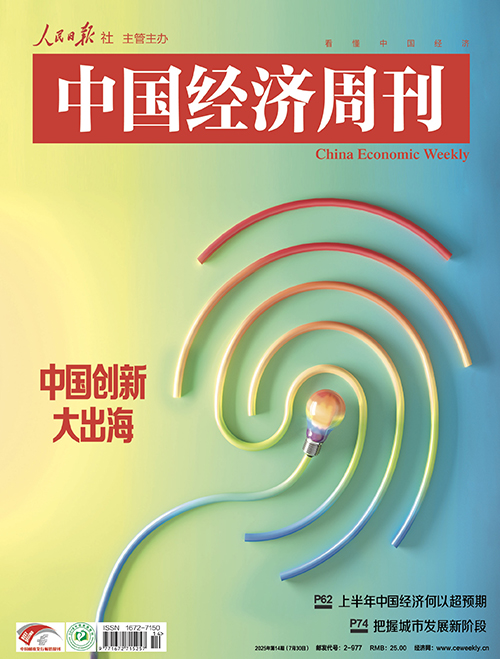本刊记者 王红茹|北京报道
7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对新时代城市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与2015年召开的上一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相比,本次会议的召开背景已发生深刻变化。到2024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67%,城市大规模扩张的“高潮期”已过,增速明显放缓。
中央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召开城市工作会议?此次城市工作会议重点解决什么问题?会议释放哪些信号?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高国力。

首提两个 “转向” 明确历史方位
《中国经济周刊》:相比10年前,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的背景是什么?
高国力:2015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时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但同时暴露出诸多问题,“大城市病”日益凸显、城市发展方式粗放、新城新区盲目扩张等现象普遍存在。
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即将突破70%这一关键节点。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率超过70%后,增长速度将逐步放缓。
在此背景下召开这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是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对我国城市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会议更加突出目标导向,在继续防范和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同时,对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市发展的战略方向和重点任务等作出更加具体的部署。
《中国经济周刊》:会议指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两个“转向”的重大判断,对城市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高国力: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作出的两个“转向”判断,是对我国城市发展历史方位的精准把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第一个转向是“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这一判断既符合世界城市化进程的普遍规律,也契合我国当前城镇化发展阶段特征。快速增长期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和速度提升,而进入稳定发展期后,虽然增速放缓,但更加注重结构优化、功能完善和新旧动能转换。这意味着城镇化工作的重心将从过去追求规模、速度、比重,转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提升。
第二个转向是“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一判断基于我国城镇化进程的现实基础和特征。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城市硬件设施、公共服务以及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已基本完成大规模建设阶段的任务。特别是随着国土空间规划对城市增长边界的刚性约束,传统的粗放式扩张模式已难以为继。这一转变倒逼城市必须立足存量空间,通过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应用,推动空间优化、结构调整和功能升级,实现资源要素的提质增效,从而保持城市持续发展的活力。
优化城市体系夯实城市发展空间布局
《中国经济周刊》:这次关于城市群和都市圈有了新提法——“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什么是组团式、网络化?
高国力:“组团式、网络化”这一表述并非全新概念,但其作为“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定语确实是首次出现。
我国作为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新型城镇化不可能在所有区域同步推进,必须坚持集中、集聚、集约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就是“组团式”发展,即以中心城市为节点,集聚人口、产业及相关配套设施,形成区域增长极。具体到我国国情,这体现为19个城市群构成的宏观组团格局。
从空间尺度来看,这种组团式发展具有双重维度:在全国层面,19个城市群相当于19个大型组团,未来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产业、要素集聚将主要在这些区域拓展深化;其他区域则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区位条件和功能定位的不同,推动城市差异化布局。
“网络化”则强调组团间的立体联通:一方面,通过高铁、高速公路、航空、信息网络等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实现城市群间的互联互通,促进劳动力、商品、资金、技术等经济要素流动;另一方面,各城市群内部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和数字网络强化次级组团间的联系。
这种多尺度、立体化的网络结构,既包含国家级城市群之间的宏观网络,也涵盖城市群内部的微观网络,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城市群发展架构。
《中国经济周刊》:此次会议再次提出“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怎么理解县城在城乡融合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高国力:2022年5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凸显了县城在城镇化格局中的战略地位。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显著,19个城市群虽然构成了城镇化的核心引擎,但广袤国土上分布的1800多个县(县级市)和2万多个镇同样承担着重要功能。
这些区域不仅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边境安全的重要支撑,更是吸纳农村人口就近就地转移的关键载体。近年来,随着超大特大城市生活成本上升,中西部地区已出现人口回流现象,这进一步凸显了县城在促进就地城镇化方面的“蓄水池”功能。
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应当采取“抓两头带中间”的发展策略:一头是以城市群、都市圈为重点,培育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引擎;另一头则以县城为基本单元,搭建城乡融合发展的桥梁。
这种双轨并行的城镇化路径,既避免了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又能通过县城的提质升级带动乡村全面振兴。在此框架下,各地大中小城市可根据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以及产业基础,形成特色鲜明、功能互补的城镇体系,共同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格局。
建设宜居城市 彰显人民属性
《中国经济周刊》:关于宜居城市,此次会议提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新模式主要指什么?
高国力:过去粗放式城镇化发展导致部分城市存在大量闲置、低效的房地产资源。当前,我国城市房地产存量规模已相当可观,人均住房面积和户均套数均达到较高水平。此次会议为房地产行业转型指明了方向,未来将重点推进存量资源的分类消化、盘活和整合利用。
具体而言,在保障性住房方面,可通过政企合作机制,将部分过剩商品房转化为保障性住房。政府应发挥引导和支持作用,企业则需主动调整经营策略。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带来了巨大的保障性住房需求,包括配售型商品房、租赁型住房和公租房等多种类型。但现实中存在供需错配问题,亟须打通商品房与保障房之间的转化通道。
在改善性需求方面,随着降首付、降利率、减税费等政策实施,市场已呈现积极变化。建议根据不同城市特点,针对市民改善性需求实施精细化政策,持续释放盘活住房存量、提振市场的积极信号。
《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会议提出“加快城镇棚户区和危房改造”,这次会议提出“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
高国力:过去10年,我国各大城市在“棚户区”“城中村”“危旧房”方面的改造已取得显著成效,但相关工作仍需持续推进。
从“城中村”改造来看,虽然许多城市已实施大规模整治,但由于城中村本质上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产物,即在城市建成区内仍保留集体土地性质的特殊区域,不同城市的改造进度存在差异。部分城市的主要改造任务已基本完成,而另一些城市仍面临较大改造压力。
至于“危旧房改造”,其范畴更为广泛,不仅包括存在安全隐患的老旧住房,还涉及小区基础设施的整体改造提升。
此次会议重点突出危旧房改造,是要求优先处置建筑年代久远、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即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危旧房改造仍是一项重要任务,需要与老旧小区改造统筹推进,分类施策、分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