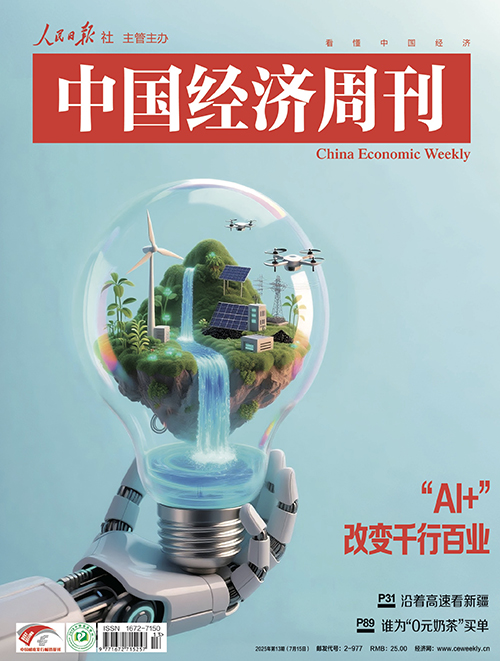本刊记者 郭霁瑶|江苏南通报道
6月17日晚上9点半,江苏南通张謇企业家学院的一间教室内,说笑声格外清晰。结束一天充实的课程后,十几名学员并未散去。他们将办公桌拼接在一起,围拢成一个临时的交流区。
“‘企二代’这个群体很特殊,我来这里也是想寻求共鸣。”湖南湘江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玲在自我介绍时说,“我是带着问题来的,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接班的经验。”
话音落下,周围几名年轻的企业负责人轻轻点头,相互交换了一个了然的眼神。
“爸爸的企业现在陷入停滞。我来培训就是希望自己尽快成长,有机会接下爸爸的接力棒。” 一名年轻女生说。
这是新时代民营经济人士培育赋能第五期培训班(以下简称“培训班”)的一个普通夜晚。这个夜晚本该随着一场讲座的收尾而结束。但对于这群正从父辈手中接棒的青年而言,关于责任、接班与身份认同的讨论,才刚刚开始。

民企代表自发组织交流 本刊记者 郭霁瑶I摄
“企二代”接班,烦恼不少
交流会上,一位来自北京40多岁的“创一代”感慨道:“我觉得‘企二代’有天然优势。最起码上一辈对你们有信任,愿意给你们机会,你们只要大胆努力做就行。”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与外界想象的“亲子信任”优势不同,“如何赢得父辈的信任”恰恰是许多“企二代”接班路上必须攻克的难题。这也成为培训班学员们课余交流的热点。
“我最常思考的是怎样让父辈对自己放心,到底怎样做才能获得全面肯定。”陈玲向本刊记者坦言。这种寻求认可的迫切感,并非个例。
讨论环节,一位“90后”女生显得有些紧张。她一手紧握笔记本,一手微微攥拳,声音带着些许迟疑:“坦白说,我还没真正进入家族企业,之前一直在国企工作。”私下里,她向其他学员透露了更深层的困惑:父亲从未明确表达过接班意愿,家里兄弟姐妹也都没进入企业。“我爸让我来培训,可能是个信号?但我真不敢问。”
这种对父辈意图的揣测和沟通的谨慎,在“企二代”群体中并不少见。
一位穿着休闲格子衬衫、喝着奶茶,20多岁的男生接着发言。他谈到,父辈管理者很少主动传授企业经营技巧,很多事情需要自己摸索,“栽了跟头才知道怎么做”。他半开玩笑地提议:“‘企二代’接班其实问题不少,之后大家可以组个局好好‘吐吐槽’。”
另一位学员的情况更为特殊。“我不是作为子女接班,是作为侄子参与公司管理。如何处理和上一辈的关系,是我一直思考的重点。”
陈玲坦言,她和父亲之间曾有一段相互试探期。“我和我爸的个性其实挺像的。那时候公司的事,我不敢直接问,他也不主动说。我总担心自己哪里没做好,爸爸是不是对我不满意。说一句话,都会回过头来注意我爸的脸色、眼神。”
在她看来,父辈的“不放心”主要源于对年轻人阅历和抗风险能力的担忧。“很多‘企二代’被保护得很好,这是父辈的爱,但也容易让他们觉得我们缺乏历练,经不住风浪。”

陈玲参加马拉松
“首先是同事,再是父子”
“老一辈总是不放心,干到‘老态龙钟’才交班,结果让年轻一代失去机会。”6月17日,太平洋建设集团、苏商集团创始人严介和在张謇企业家学院发表演讲时说。
严介和提到的“不放手”困境固然普遍,但并非没有破局者。一些较早获得信任和机会的“企二代”,已经在实践中摸索出了自己的成长路径。
田鸣宇是河北一家面粉企业的“企二代”,在他看来自己算是“幸运儿”。“我们家老爷子挺愿意放权的。很早就把机会给到我。”他笑着说。在介绍企业成绩时,他还是保持着清醒的谦逊,“当然这是老爷子打下的基础,我也就是替他‘吹牛’,这不属于我的成就”。
据他介绍,目前公司国内业务被划分为两大板块,由田鸣宇和父亲各自独立管理。“市场、区域、工厂还有队伍完全分开,互不干扰。”
独立运营意味着独自承担。“我们行业固定资产投入大,银行贷款、设备折旧压力重,加上前两年疫情影响,挑战非常大。”他说,正是这种被“逼到悬崖边”的处境,促使他蜕变重生。目前,他负责的板块销售额约60亿元,父亲的板块在120亿元左右。“我爸说,等我把自己这块干得更好,再去‘收编’他的板块,这样接班就顺理成章了。”
每个企业的接班模式各不相同。陈玲选择的是一条“从基层做起”的路径。2008年大学毕业后,她便进入父亲的企业,从基层一步步走到今天的管理岗位。
她至今记得自己参与的第一个风电项目。由于项目地处偏僻的黄海边,为了方便工作,陈玲选择租住附近的农房。“房子漏风,地面都是泥土,夜里甚至能看到蜈蚣爬进来……那种环境,想起来都头皮发麻。”在那里,陈玲坚持了一年多。“我爸安排我去,我就去了。那时就想,如果退缩了,他更会觉得你扛不住事。再难也得熬过去。”
企业的交接不仅关乎业务划分,更深层次的是两代人角色认知与沟通方式的转变。采访中许多“企二代”都提到,和父辈之间需要建立超越普通家庭关系的互动规则。
淮海控股集团副董事长安桂辰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在企业里,我们首先是同事,不能只用父子关系来看待。不能说他是老爸,我是儿子,在家里怎么样,在公司层面也这样。既然他是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我就会用专业的方式跟他沟通工作。现在我们也建立了互信的交流模式,既保证专业,也不能影响父子感情。”
陈玲对此深有体会,她和父亲的沟通模式也经历了演变。最初是父亲手把手教她如何做;渐渐地,陈玲开始带着问题去请教父亲;后来,能带着自己的方案想法去讨论。“现在我已经能独立决定如何处理工作,向我爸汇报一下工作进度就行。”
第一件事是练好方言
赢得父辈的信任,并不意味着接班之路就此平坦。在车间、在工地、在日常管理中,“企二代”们很快会面对另一群关键人物——那些跟随父辈“打江山”的“老臣”。和他们的相处是“二代”们面临的另一道现实考题。
有“企二代”坦言不知如何拿捏对老员工的态度分寸,也有人苦恼于调和“老臣”与“新臣”的关系网络。
“95后”王晨对此深有体会。2022年正式进入自家企业时,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巩固方言。“公司里老员工习惯用方言交流,开会也几乎不讲普通话。语言不通,怎么融入?”他解释道。
一位来自中部的“企二代”则遇到了更直接的挑战。他回忆刚进公司时,部分老员工表现出不适应,“我一安排工作,就有老员工以休假为由推托。”这种细微处的“试探”,曾一度让他十分头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与父辈偏好凭借经验阅历做事不同,许多“企二代”更倾向于制度化管理企业,比如引入新的办公室软件、建立效率流程等。
陈玲认同制度的力量。“老员工是公司的财富,别指望一进来大家就必须听你的。关键还是制度管人,流程化运作。”
除了制度,“企二代”们也在尝试用新方式凝聚团队。陈玲是马拉松爱好者,今年湖南娄底举办赛事时,她鼓励员工报名参与。“不少老员工私下努力练习,下班就去跑步。”令她欣慰的是,有老员工完赛后感慨拿到了“人生第一块奖牌”,回家后孩子都激动不已。“员工的精神面貌好了,企业氛围也好了不少。”
回顾自己的接班历程,陈玲心态已然不同:“以前总想证明自己,现在平静多了。在企业里,担起责任,做好该做的事,就够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田鸣宇、王晨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