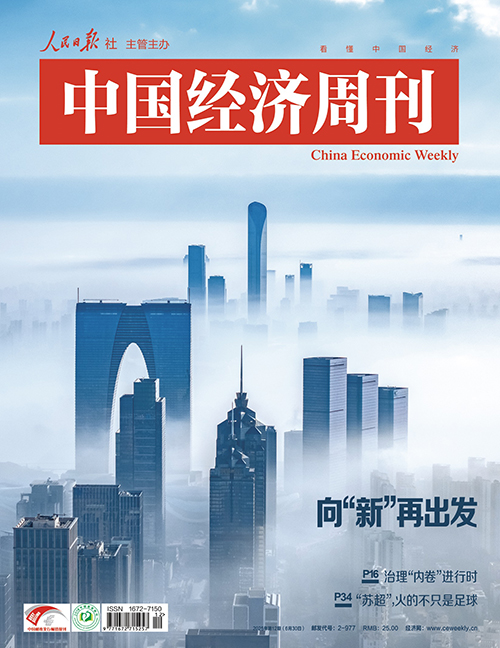文|尹稚
202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这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城市更新工作作出的全面部署。就大家比较关注的两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尹稚
新型城镇化“下半场”的主战场变了
中国城镇化的“上半场”实现了数亿人口从乡到城的转移,催生了大量新城新区的建设,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在人类历史和城乡建设史上可称之最。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人口分布和社会形态完成了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的转型,城镇化率从1958年时不足18%上升到2024年的67%。这是巨大的成就,也是未来走向共同富裕的“城乡中国”的坚实基础。
随着中国人口总量的增速和城镇化率的增速相继迈过拐点,我国城镇化率从快速增长向稳定发展转变。
考虑到生产、生活、生态的平衡,以及城乡共同繁荣和粮食安全、国土安全的需要,城镇化率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达到75%左右较为现实,此后将进入一个稳定的“平台期”。
这样一来,以当前的城乡人口基数看,从乡到城的人口转移净新增量也就还剩1亿左右,而生活在已城镇化建成环境中的人口会稳定在10亿左右。
这组数字说明,城镇化下半场新城新区的建设规模,最大也就是上半场的1/7。与此同时,城市更新行动所惠及的人口基本盘是这个量的10倍。
所以,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变了。
城市更新行动是与城镇化进程永续相伴的。伴随着时代进步和人类对美好生活追求,新的需求与存量环境之间不匹配所产生的“城市问题”会不断地暴露出来,所以“城市不死,更新永续”。
在中国的实践中,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强调的“城市更新”,已成为解决城市发展难题的长期指导理念,与中国城市走向现代化和城市人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一直相伴。
“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全民参与”的多元主体“共同缔造”是城市更新的时代特征,也是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进程。
在这个进程中,“有为政府”的重要任务是明确实现发展诉求,把控全局观和长远观坚守下的战略级留白,建立多方获益的规则,尤其应实现产权、利益的认定和交易规则的建立,并立足公共利益,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均衡。
“有效市场”的内涵可以理解为以质量求增量、谋发展,实现存量资产增值、社会财富放大,重组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流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也包括承担社会责任、扶贫济困、救助弱势群体。
“全民参与”则表现为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完成理念、组织、行为的提升,建构新的以自觉、自愿、自适应为特征的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社会生态。
总之,改变当下城市更新中多为政府主导的局面,通过“共同缔造”理念做深做实,促进多元合作,激发城市更新行动中人民群众的创新活力和市场动能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新型城镇化“下半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转变城市发展模式的核心所在。
而且,城市更新不仅仅是城市发展模式的变革,也是城市治理方式的变革,存在不少制度创新的机会。“无体检不更新”这个口号的提出,就是让我们在侧重“补短板”的角度去发现“城市问题”,同时也要从“谋发展”的角度发掘新的社会需求,所以城市更新行动的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是并重的。
更新项目本身的千差万别也凸显出规范更新流程、稳定中长期市场预期的重要性。更新工作涉及领域多,则促使我们思考如何打通环节堵点,实现诸如土地政策、建设规制和财政金融政策的跨部门协同。
在“无人区”的白纸上进行新区新城建设的传统规划工作,变成了在“有人区”干活,这就需要明晰物业权利、人的权利和义务,在规划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给予社会资本参与城市更新的合法地位,畅通参与路径也是亟待突破的制度创新环节。“运营前置”不是简单的流程调整,而是成果利益分配机制的调整、资源调配及测算方式的变革,由此也催生了对新型金融工具创新的“呼唤”。这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显然需要更广泛的部门协作和更有力的协同引领才能实现。
所以,城市更新是新型城镇化“下半场”中一项十分重要的行动,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工作重心之一。城市及其区域的发展能力和品质提升,也将是从“城市中国”走向共同富裕的“城乡中国”的重要抓手。
城市的人口基数、内需市场大,创新动力强,支撑人类自身发展和代际提升、能改善国民素质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体系优势强。通过城市更新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城市中国”的时代特征绑定,并为未来“城乡中国”的共同繁荣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做充分的准备,无疑是有巨大价值和美好前景的。

江西省丰城市
健全多元化投融资方式
城镇化上半场建立的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为新城新区建设提供了可靠的资金支持。下半场中,在有限的新城新区的建设中,这种模式仍可持续。新的问题是,面对大量已建成环境,即“存量土地”,改造提质的钱从哪里来,这需要更多元化的渠道去解决。
《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提出的八项任务大体上是功能性分类的阐述逻辑。谈到城市更新的钱从哪儿来时,还有其他分类逻辑——一种是按商品、半公共品、公共品分类,另一种是与盈利、微利、非盈利相对应,通过差异化的施策去找钱,抑或设计形成新的金融工具。
例如,支撑性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生态性基础设施大部分具有鲜明的公共品和非营利特征,其本身是不赚钱的。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加大地方政府财政投入是其主要来源,新的超长期国债这种金融工具的设计也是有力支撑。
而所有可以在市场上实现“优质优价”的项目则具备明显的商品属性,在明确其商业可持续前提下,完全可以走市场化的投融资模式,租售并举,获得可持续的社会资本投资。
为了获得运营收益,解决投资回报周期长的问题,可以利用中长期专项债券、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资产证券化产品等新的金融工具,以达成更好的风险可控。半公共品则体现在政府财政投入与社会资本投入的结合,以及金融工具的混合使用。
具体来讲,为了实现城市更新项目的可持续运营,经过多年实践,我逐步形成了以下认识:
一是国有资产处置问题。依据成功实践经验,在城市更新中,将轻资产与重资产进行分离是最主要的出路,套用传统“投入—产出”的模型是行不通的。
二是民营资本进入城市更新,要谨慎无兑价(即没有相应的交换价值或补偿)进入城市更新领域。重资产的产权纯粹性非常关键。
三是关于政府对城市更新投资的引导。要关注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行为,大型国有资管平台在城市更新中机会更好一些。同时,可以考虑打破当前的一些壁垒,引入保险资金。城市更新需要“耐心资本”,追求稳定现金流和稳定回报的险资,可能是较为匹配的资本类型。
更加注重运营也是解决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在规划中,应当将运营作为设计之外的第二个核心,在传统设计环节中嵌入资产甄别、运营策划等内容。
例如,运营团队不仅仅要确定更新的整体思路、立意、实施路径,还要对空间开闭、动线、调性(三者均为建筑与室内设计的专业用语)的设计形成合理的指导性意见,同时也应参与对项目价值的评估和更大范围的规划研究。这些都可以作为实施规划的基本前提。
总的来说,应当以运营思维寻找和确定项目的社群与消费,配套相应的业态资源,并综合业态类型进行空间规划和建筑设计,最终形成运营牵头、设计配合、规划兜底的中微观“新规划”路径实践。
(本文作者系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