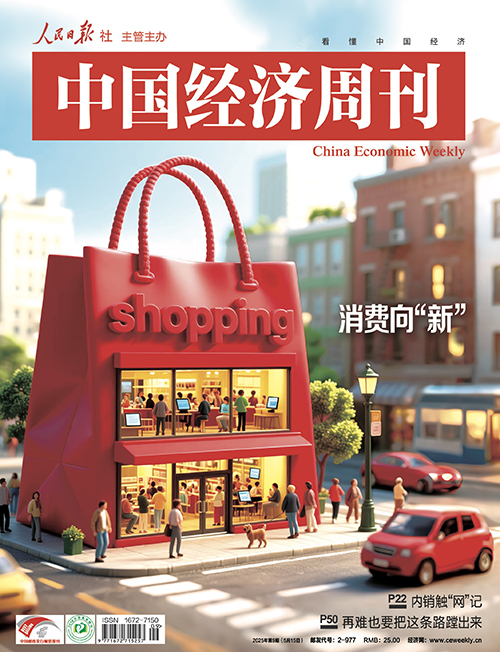本刊记者 孙晓萌
今年1月以来,美国政府与多所大学因高校管理问题发生冲突。5月5日,美国教育部长宣布,哈佛大学不再获得任何联邦资助,这是自哈佛宣布起诉美国政府后,又一次事态升级。
在近期的政治压力下,美国顶尖高校开始抛售私募股权及流动性资产,引发市场对高校“长期资本”可持续性的担忧。要知道,美国大学捐赠基金总规模达8737亿美元,这些资金在高校运营中举足轻重。其中,耶鲁捐赠基金规模414亿美元、哈佛520亿美元,资产量庞大。

打出 “资产抛售+发债” 组合拳
高校捐赠基金是指通过校友及社会捐赠设立的长期性资本池,以“捐赠者意愿”为约束,将本金永续保留,其收益用于支持高校运营,是一种独立基金体系。
2024年度NACUBO-Commo-nfund(NACUBO是美国高校经营管理协会,Commonfund是咨询机构)联名报告显示,高校捐赠基金规模上,哈佛大学居首位,得克萨斯大学以约475亿美元居第二,耶鲁紧随其后,普林斯顿、斯坦福、麻省理工分列第四至第六。
今年4月,耶鲁大学宣布正在出售私募基金份额,交易规模或达60亿美元,约占其捐赠基金的15%,这是耶鲁首次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资产清算。
几乎同时,哈佛大学被曝与杰富瑞等机构洽谈出售约10亿美元私募基金股权。彭博社称,哈佛管理公司负责此次交易,洽谈对象或包括Lexington Partners等买家。据悉,哈佛私募与风险投资配置比例接近40%,流动性资产比例相对较低。
除了直接抛售私募股权,这些高校还试图通过发债缓解压力。近期,麻省理工学院拟发行7.5亿美元应税债券,斯坦福与普林斯顿分别发售了3.27亿美元及3.2亿美元债券,耶鲁也在考虑用债务工具分散流动性风险。
业内认为,此番罕见的“发债+资产抛售”组合拳表明高校对未来的联邦资助和税收政策走向高度不乐观,也暴露出高校传统依赖资本市场资助运营的脆弱性。
“耶鲁模式”并不抗压
NACUBO-Commonfund数据显示,2024财年,658所美国院校捐赠基金对股票和实物资产投资比例最高,占55.7%;私募股权配置占比17.1%,风险投资11.7%。2023财年和2024财年,小型高校捐赠基金对公共股权市场的投资占比较大,取得了较高回报。较大规模的高校捐赠基金则对私募市场更为重视,投资也更加“激进”。
如果谈到投资比较“激进”,就绕不过“耶鲁模式”。
它由耶鲁前CIO大卫·斯文森倡导,鼓励高校将60%以上的资产配置于另类投资,以获取超额收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耶鲁的捐赠基金都是运营最成功的高校捐赠基金之一。但近年来,由于私募市场回报率落后于公募股市,使得“耶鲁模式”受到诸多质疑。
该模式也比较容易受到外部压力影响,此次抛售就是受外部政治压力所致。此前,美国政府借高校改革之名,冻结多所名校逾百亿美元联邦研究经费,并威胁撤销高校免税资质,直接冲击高校的资金来源。因此,哈佛、耶鲁等学校被迫寻求预备性融资,以对冲随时可能到来的资助中断,支付起诉政府的法律费用。
自2022年以来,私募市场退出渠道趋向收窄,资本分配与回收速度显著放缓,折价抛售成为机构缓解流动性紧张的主要手段。同时,发债仍被视作比大额折价抛售更优的选择,这次多校才会选择“发债+资产抛售”搭配。
此次哈佛、耶鲁这类大型机构投资者(LP)抛售大量私募股权,业内认为势必加剧市场的供给压力,导致买家要求更大折价,对整个私募行业的资金循环极可能造成负面影响。
市场进而担忧,这种骨牌效应可能波及更多机构投资者,令私募基金面临再融资困难,抑制未来的交易。不少人担忧,如果美国政府继续打击高校,顶尖大学的资产抛售行为很有可能成为风暴眼,引发市场一连串反应,为美国带来“新次贷危机”。
长期以来,依据美国《国内税收法典》,美国绝大多数高校可享受税收豁免资格。但是在2017年,美国政府通过设立《减税与就业法案》对大学捐赠基金征税。在法案规定下,如果一所私立大学,每名学生享有的捐赠基金平均规模超过50万美元,政府就要对捐赠基金的投资收入按1.4%征税。
今年,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提议将该1.4%税率提高到14%,这些富裕的捐赠基金也再次成为税收目标。若政治干预常态化,不仅捐赠基金的运营与投资将受制约,美国高校的日常管理也势必受到影响,他们的出路又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