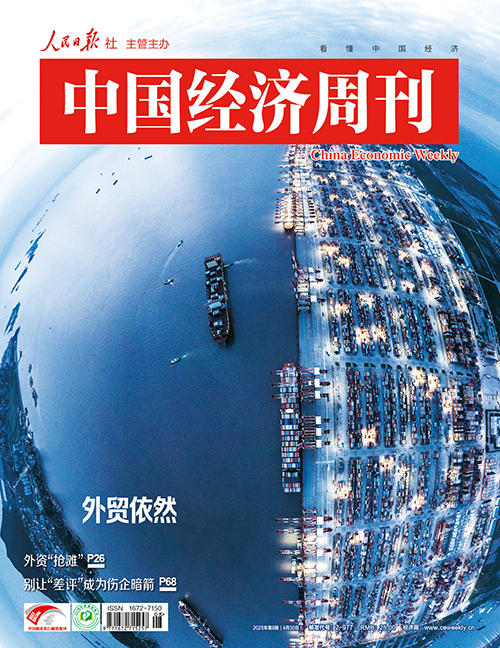经济网网友“小禾苗”: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要多措并举促进价格合理回升。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到了这一点。一般而言,老百姓不太喜欢物价上涨。促进价格合理回升有什么深意?对宏观经济有什么影响?
近期,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实际GDP增速始终保持在5%左右的合理区间,但价格指标如CPI、PPI、GDP平减指数在相对较低的位置运行。即使将各类价格指数综合考量,当前价格总水平仍处于历史相对低位。这种“量价背离”现象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既往增长周期中,当实际GDP增速达到预期目标时,价格指数往往会同步回升,企业利润也会持续改善。当前这种GDP增速与物价水平背离的现象较为少见。

伍戈
“量价背离” 如何产生
量和价不是天然吻合的。很多行业、企业有“以价换量”的共同特征,即通过降价换取市场份额,实现量的增长。但这种持续的价格下行可能会削弱市场信心。因此,我们期待看到一种量价协同上升的良性循环。
为什么企业愿意“以价换量”,即便降价也要生产?
降价和总需求较弱有关。微观经济学中有个和宏观领域相似的场景:面对产品售价持续走低,企业非但不缩减生产,反而选择“逆周期扩产”。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暗含精密的成本核算逻辑。当商品售价仍然高于可变成本时,即便无法覆盖固定成本,企业仍会选择继续生产。(注:可变成本指随产量增减而变动的成本,如材料费;固定成本指不随产量变化的成本,如房租)一些很“卷”的企业甚至会一边降价,一边扩大生产。此时企业的经营目标已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亏损最小化”。
我们最近统计了一些上市企业的状况。企业产品售价低于总成本,也就是说,从经济意义上,它们是亏损的,但售价仍高于可变成本。这样的情况下,企业仍然选择生产,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量价背离”“亏损生产”的情况在现实经济中存在。
回到宏观视角。我们要汲取日本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错误教训。1990年,日本房地产经历了剧烈调整,调整之后,日本的实际GDP在波动,但实际GDP的中枢基本保持稳定;代表价格的GDP平减指数却持续下行。也就是说,实际GDP每年都可能达到预期目标,但价格指数在不断下台阶。
面对这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可能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观点是维持现有政策力度,守住实际GDP就是守住经济基本盘;另一种观点是必须重视名义GDP收缩的现实,主张采取更积极的刺激政策。(注:实际GDP是在价格保持恒定或以某一年为基准价格的前提下所计算的GDP,名义GDP是按当前市场价格计算的GDP,二者区别在于是否剔除价格变动的影响。)
当年日本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在房地产调整的前10年,日本央行没有制定具体的价格目标。只要实际GDP保持正增长,便视为经济基本盘稳固。后来日本发现这样不行,价格很关键,因为价格关乎企业利润、关乎微观主体对经济体温的感知、关乎信心。日本意识到,需要借鉴成熟国家经验,制定价格目标。
此后,日本央行决定将价格目标锚定在0至1%之间。实践表明,这样做法并没有大幅提升居民的预期信心。后来日本把通胀目标调到2%,并确立为不可动摇的铁律,该目标被明确定义为价格调控的“下限”而非“参考值”,这意味着只要CPI未达2%,超常规货币宽松政策和财政刺激就不会止步。
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日本人得出结论:量和价同样重要。经济健康并非简单的正增长即安全。2%的通胀值虽然是个经验数据,但对于提振日本老百姓的预期信心非常有帮助。
CPI 2%左右涨幅目标非常务实
去年全国两会设定的CPI涨幅目标为3%左右,而今年则调整至更贴近现实的2%左右。这是一种很务实的做法。同时,中央在诸多文件中也反复强调了对价格的关注。虽然重视,但价格在实际政策中的权重有多大?
去年,包括央行行长在内的多位领导曾多次提及推动价格温和上涨。但从后续的价格走势来看,尽管领导层对此给予重视,价格在实际政策中的权重仍有待提升。
从计量回归分析来看,无论是中国的货币政策规则还是财政政策规则,目前对GDP“量”的权重都超过了对“价”的权重,价格的权重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展望2025年,我们的目标是实现约5%的实际GDP增长,经过努力,这个目标是可以达成的。如果今年我们想要实现GDP平减指数转正,也就是大于0,这可能需要超常规的政策力度来推动。2024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价格目标的权重大小。如果价格权重较小,我们或许只需常规努力便可实现5%的GDP增长目标。如果我们有更广义的目标,包括价格考量在内,那么所需的政策力度可能不仅仅局限于目前讨论的政策框架。
(本文作者系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