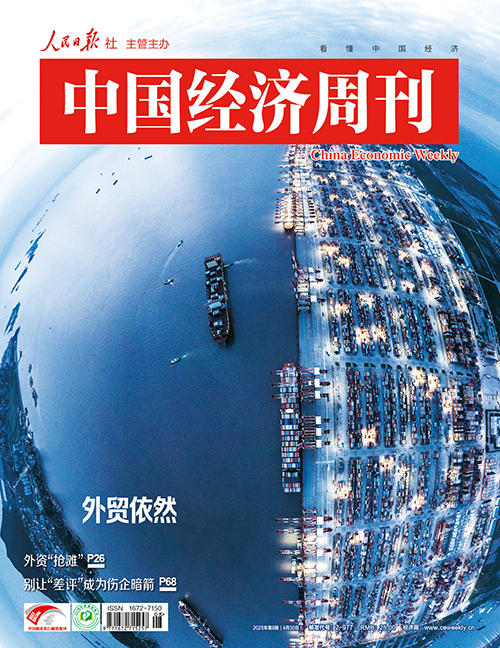本刊记者 石青川

本刊记者 石青川I摄
4月18日清晨6点,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厂房内,加热炉、粗轧、精轧等设备有条不紊地工作着。数万平方米的自动化车间里,鲜少看到工人的身影,所有机器的运转全靠控制室里的数个按钮与摇杆。工作了一夜的何希家仍在控制台里操作,盯着数块屏幕上跳动的数字,精准地控制每一个参数。
身为高级技工的他已经在西南铝业工厂和这些连轧机打了18年的交道,今年他刚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18年里,何希家见证着“劳动”这一概念的变迁。从当年手动的运料填料到如今的自动化操作,从零点几的容错到现在零误差。“以前学习工艺的传承,现在钻研技术的革新。”何希家说。

工作中的何希家

西南铝业刚生产出的铝卷 本刊记者 石青川I摄
“眼睛就是尺”
2007年,何希家第一次接触“铝”这个产业。尽管是部队转业,但何希家看起来更像是个学生。“不太爱说话,但爱问问题。没事就看书,拿着个小本本,抄抄这、记记那。”这便是何希家的师父朱雪兵对他的第一印象。
彼时中国制铝技术还很粗犷,高精度铝几乎只能进口,工厂里用的设备也只能进口。外国专家匆匆忙忙的技术指导与设备上大量的外文专业术语,让朱雪松与何希家师徒俩完全不明白怎么使用。
连轧机全套设备的操作台有50多个按键、摇杆,10多个显示屏,连轧机主操手不仅要对各个按钮与摇杆了如指掌,还要熟悉铝材在不同温度的特性以及每台轧机的性能。
“所以我就拿小本本抄下来,然后查书籍,查好后记下来,再去设备上对照。”何希家说,这就是为什么师父朱雪兵说他像个学生的原因。“这也是师父教我的,遇到困难,不要急躁,不知道怎么办时,就用最笨的方式去摸索。”
师父朱雪兵曾获得“全国技术能手”称号,他有一个“眼睛就是尺”的绝活儿。
“铝卷生产出来后,一眼就能看出合不合格,如果不合格还能判断出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说起师父的这个绝活儿,何希家满是自豪。因为这个绝活儿,他也会。
朱雪兵的其他徒弟,大多等着师父把操作步骤画成示意图,然后依葫芦画瓢学习,但“好奇宝宝”何希家不一样。“那段时间都被他整烦了,只要我上班,除了上厕所,其他时间走哪儿他都跟着。有时我不在,他逮住别的前辈也要刨根问底。”朱雪兵说,这是他带过“问题最多”的学生。
也是这些问题,让何希家不仅快速掌握了机器操作的步骤,甚至还能教其他师兄弟。最终他也练就出“眼睛就是尺”的绝活儿。
“眼睛能判断的误差跟电脑比不了,现在这个技能用得越来越少了。但技能学习的过程也是一种工艺的传承。”何希家说,耐心、不急躁,遇到困难不介意用最笨的办法摸索,这就是工艺传承的内核。
用最笨的办法找到最佳的方式
朱雪兵传授给何希家的“笨办法”让他攻克了一项技术难题。
铝卷的生产必须具有连贯性,如果中间出现小的差错,所有步骤与数据就都要重新调整,最前面已经进入工序的那一截就不得不作废然后重新加热。因此稳固工序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而PS铝基版生产对精度要求极高,热量、受力等不均匀时,非常容易形变,有时候还会因为机器原因出现粗条纹,有这些差错的PS版都不能用,要重新轧,因此生产效率低,成本高。
为了消除这些小差错造成的大损失,何希家每天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操作,详细记录每一个可能影响铝材的参数,再通过成品判断这些参数中哪些影响最大。
通过最笨的办法,日复一日地试错、判断、调整,最终何希家找到了最佳的精轧方式,并将其稳固下来,不仅生产更快、质量也更高。
用同样的笨方法,何希家还创立了“何希家操作法”超宽罐体料生产技术,攻克CTP版基热轧材料晶粒粗大缺陷,减少产品生产周期3天以上,实现了国内CTP版基直轧生产工艺“零”的突破,年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
朱雪兵说,以前这些精度要求高的产品,当班产出二十几块就会给生产奖励,现在稳固了工艺后,每一个班次最低都能生产出五十几块。徒弟的优秀也让他这个师父十分开心。
有了这些经验,何希家还积极参与7050大宽板合金热轧开发,这个项目对国防重点材料替代进口起到重要作用。
随着国产新能源汽车对铝制汽车板需求越来越大,密度只有钢铁1/3的铝,成为整车减重的替代方案。但铝板单价相对更贵。何希家说,他接下来的目标,是要用精进工艺的方式将这些车用铝板的生产成本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