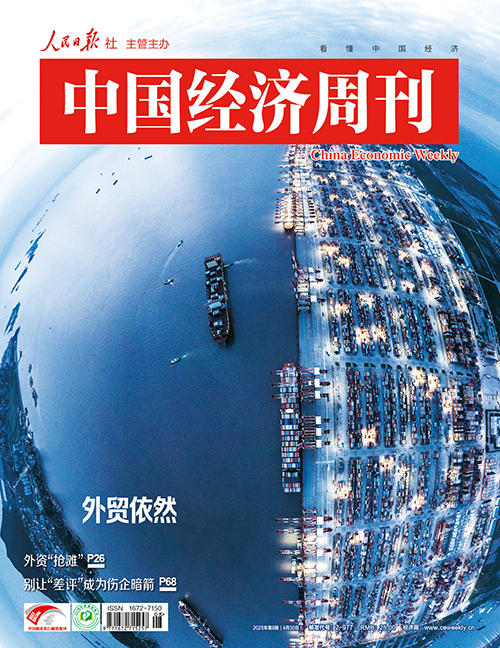本刊记者 宋杰
上海女生单媛最近领了新任务:每天她要在小红书、抖音、微博等平台搜索与公司相关的所有评价,一旦发现“产品含激素”等无事实依据的恶意差评,就立刻联系博主沟通修改或删帖。
单媛所在的这家婴童洗护类企业年销售额破10亿元,新设“舆情公关岗”,背后满是无奈。
“企业没名气时无人问津,现在规模做大了,恶意差评就像影子一样甩不掉。”单媛道出了许多企业的痛点。
上述情况不是个案。针对这些涉企网络乱象,中央网信办2025年“清朗”行动正在进行整治,剑指集纳负面信息、造谣抹黑企业和企业家、虚假不实测评等毒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营商环境。

“有人把‘差评’磨成刀”
现实中的恶性商战,往往采用最“朴素”的手法——刷差评。
差评如潮和销量暴涨同时出现,奇不奇怪?浙江绍兴某伞企曾遭遇集中下单,下单后买家均申请“仅退款”并给出差评。因收货地址和电话虚构,店铺寄出的货物大量丢失,损失不小。经查,有团队实施恶意攻击,通过虚构地址、伪造“货不对板”等理由集中刷单差评1万余单,导致伞企网店评分暴跌、搜索降权,直接损失超28万元。
南京某三明治外卖店在2024年遭遇前合伙人孙某的恶意攻击。孙某以每条差评80元的价格雇佣多人集中发布虚假差评,如“食物变质”“服务恶劣”等,导致店铺评分骤降,订单量下跌。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判决孙某赔偿3万元,并认定其行为扰乱市场秩序。
虽然这些差评最终被删除,但品牌遭受的信任危机却难以在短期内消除。
虚构产品问题、伪造消费体验、雇佣 “水军” 刷评、借算法扩散……恶意差评的手段不断翻新,而一旦“差评”变成商战工具,不仅伤害企业的利益,更透支消费者对市场评价体系的信任。上海某饭店经营者对记者说:“我们不怕真实的差评,怕的是有人把‘差评’磨成刀,专门捅向认真做产品的人。”
让 “差评” 回归监督本质
法治为正当批评与恶意攻击划定边界。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司法实践中,消费者只有基于真实消费体验的批评才受法律保护。若评价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如虚构“产品含激素”“食物变质”),即使使用“可能”“疑似”等模糊表述,仍可能构成侵权。
法律界普遍认为,“差评权”的行使应以“善意”为前提。职业差评行为涉嫌违反刑法,但如何定性,应根据其具体行为分析。
对恶意差评,各地正构建立体化治理体系。以上海为例,在“清朗浦江・2024”专项行动披露的典型案例中,“乳韵之家”“星空财富”等自媒体账号借发布企业负面信息敲诈勒索,要求付费“撤稿”或加入“白名单”。此类以谣牟利的新型网络黑产,正成为监管打击的重点。上海网信办依法关闭涉事账号,并将涉嫌犯罪线索移交公安机关,释放出 “以法治斩断‘差评勒索’产业链”的明确信号。
杭州互联网法院将“虚拟共享法庭”入驻平台、电商网红村等网络“最末端”,深圳试点“企业信用修复”机制等创新实践。前者推动司法服务直达网络治理末梢,后者助力企业清除网络谣言留下的“数字疤痕”。
法规设计亦在走向精准化: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夯实名誉权保护根基,《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要求平台建立谣言处置机制,从制度层面筑牢“真实评价”与“恶意攻击”的防火墙。
在数字经济时代,“差评”不应异化为伤企暗箭,企业也无须对正当批评草木皆兵。
单媛的电脑屏幕上,有用户更新了评论:“泵头有些扎手,设计能不能改改?”这一次,她没有急着删帖 ——来自真实消费者的合理建议,被认真记录进产品改进意见清单。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单媛为化名)